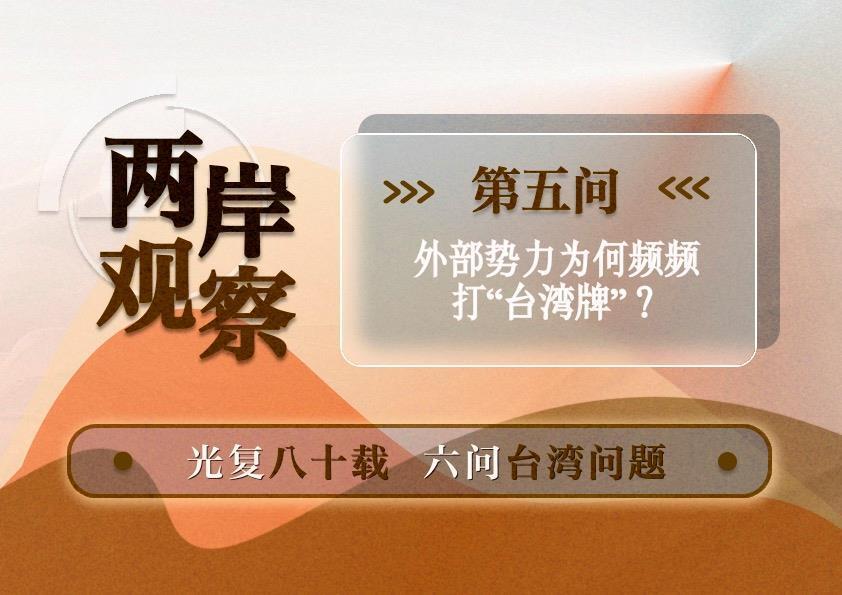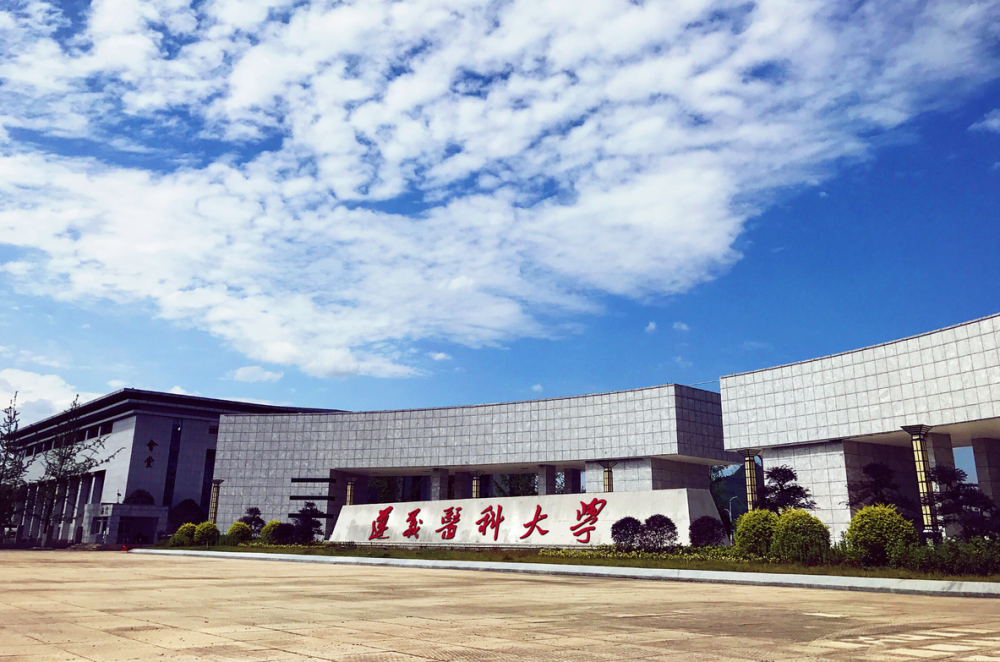那天清晨,阿纳斯跟着当地救援组织赶到一片刚被空袭的居民区。他举着相机刚要开拍,就听见人群里有人喊他的名字。回头的瞬间,邻居哭着拽住他的胳膊:“你家……你家被导弹炸了!”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,他看见自己住了五年的楼房只剩半面墙,母亲种在阳台的无花果树倒在砖堆里,枝桠上还挂着没成熟的小果子——那是上周视频通话时,母亲说要等他回家吃的。
“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,相机差点掉在地上。”后来阿纳斯在和同事的通话里说,“我拍过那么多被炸的房子,可当那堆瓦砾变成‘我的家’,我才明白,‘悲剧’这两个字,写在纸上是黑字,砸在身上是血。”更让他煎熬的是,家人虽然侥幸受伤但无生命危险,可加沙的通讯早就断成了碎片——他拍的现场画面要翻三座废墟才能找到微弱的信号,一段2分钟的视频往往要传4个小时,有时候刚传了一半,信号又没了,只能蹲在墙角重新来。
“我不怕被炮弹炸到,怕的是世界听不到加沙的声音。”阿纳斯摸了摸相机上的划痕,那是前几天躲空袭时撞在墙上弄的,“我的家没了,但还有成千上万个家庭正在经历同样的事。我多传一段视频,就多一个人知道,加沙不是‘冲突地区’的标签,是有人在废墟里找孩子的玩具,是老人抱着破碎的相框哭,是救援人员喊到沙哑的‘还有人吗’。”
战争从不是遥远的新闻标题,是记者突然失去的家,是母亲没来得及收的无花果树,是传不出去的“我很好”。阿纳斯的镜头里,没有刻意的煽情,只有真实到扎人的细节:废墟上的孩子抱着玩偶发呆,救援队员用手扒土的指甲盖渗着血,还有他自己对着镜头整理衣领时,眼角没擦干净的泪。
“我是记者,更是加沙人。”阿纳斯说,“哪怕信号再弱,我也要把加沙的呼吸传出去——因为每一声呼吸,都是活着的证明。”
此刻的加沙,依然有炮弹落下,依然有废墟升起,但总有像阿纳斯这样的人,举着设备在断壁残垣间跑。他们的镜头里,藏着战争的残酷,更藏着普通人不肯熄灭的希望——就像那棵倒在瓦砾里的无花果树,哪怕枝桠断了,根还扎在土里,等着春天再来。